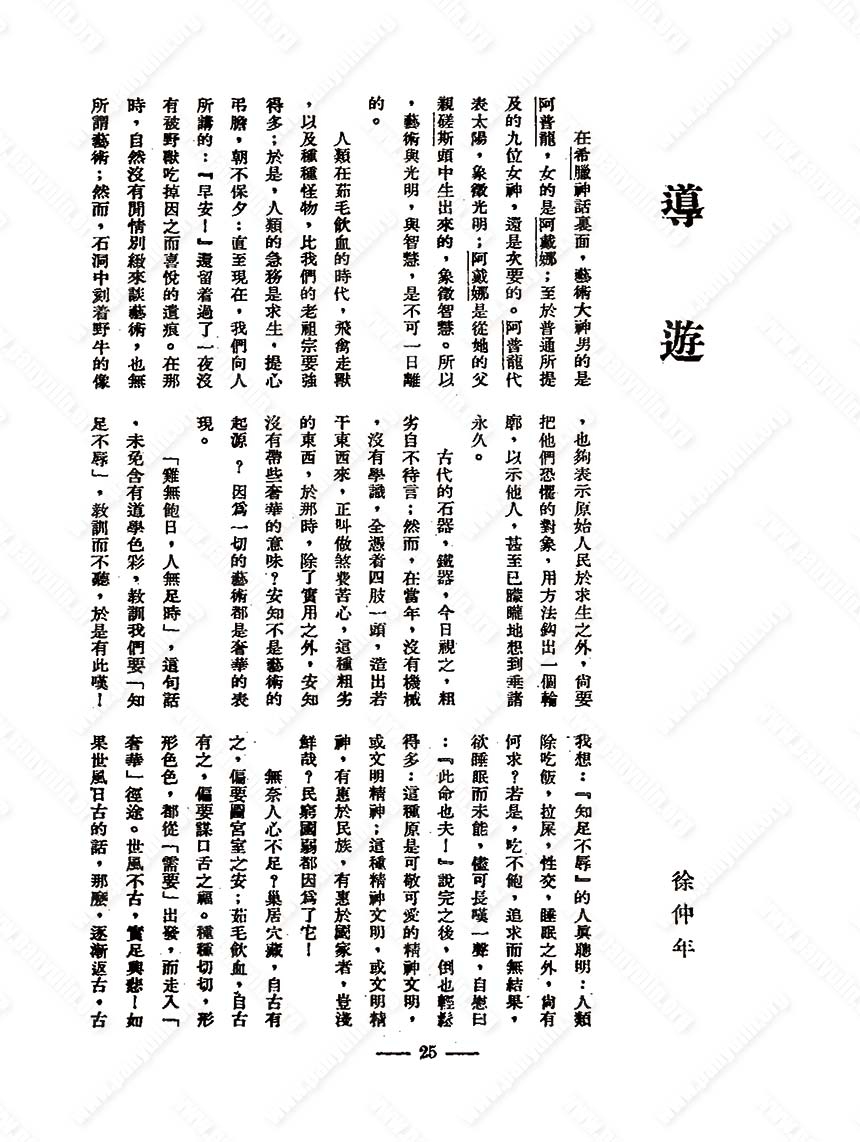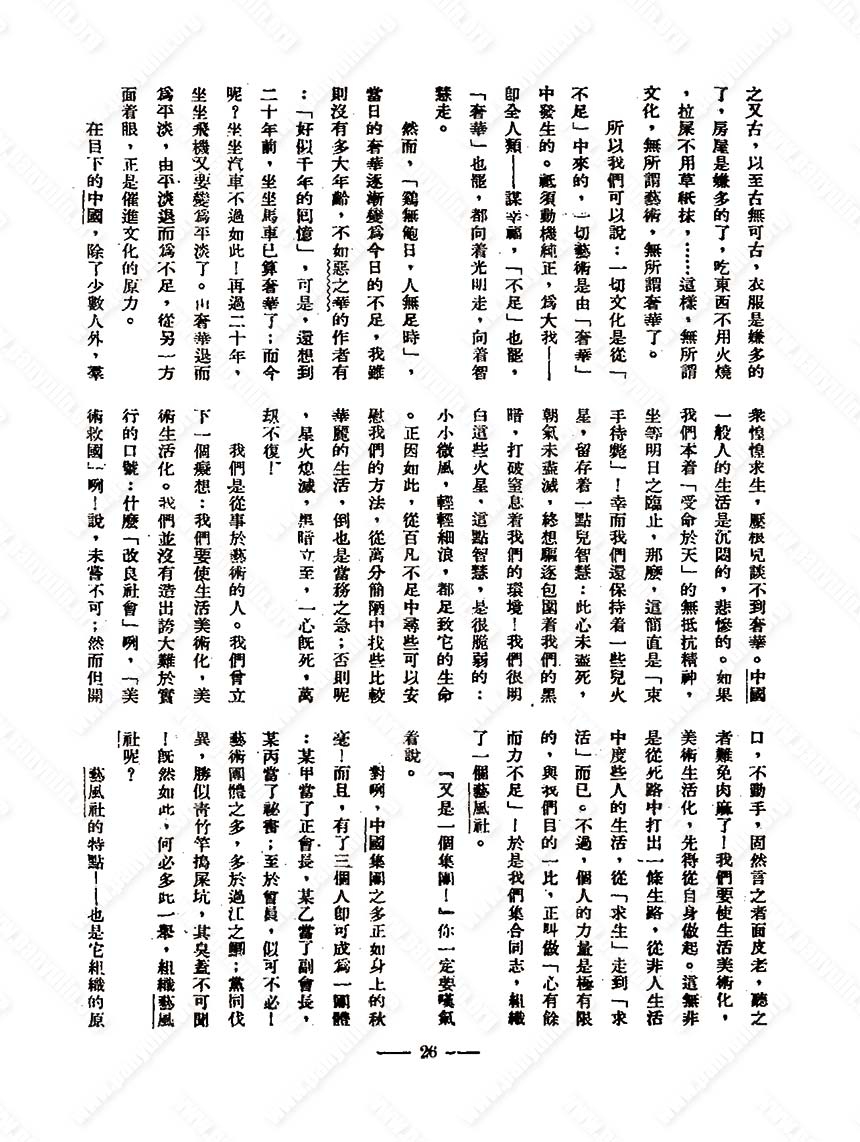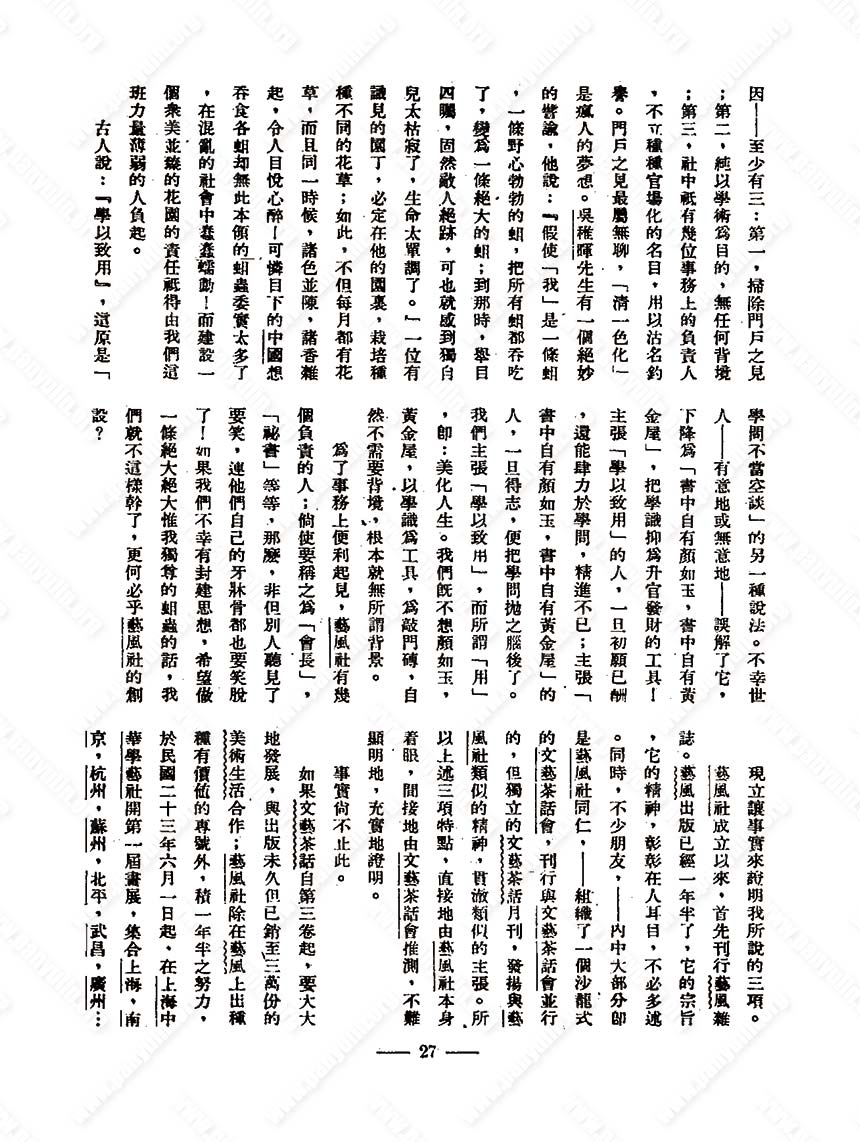在希臘神話裡面,藝術大神男的是阿普龍,女的是阿戴娜;至於普通所提及的九位女神,還是次要的。阿普龍代表太陽,象徵光明;阿戴娜是從她的父親磋斯頭中生出來的,象徵智慧。所以,藝術與光明,與智慧,是不可一日離的。
人類在茹毛飲血的時代,飛禽走獸,以及種種怪物,比我們的老祖宗要強得多;於是,人類的急務是求生,提心弔膽,朝不保夕:直至現在,我們向人所講的:「早安!」還留著過了一夜沒有被野獸吃掉因之而喜悅的遺痕。在那時,自然沒有閒情別緻來談藝術,也無所謂藝術;然而,石洞中刻著野牛的像,也夠表示原始人民於求生之外,尚要把他們恐懼的對象,用方法鈎出一個輪廓,以示他人,甚至已朦朧地想到垂諸永久。
古代的石器,鐵器,今日視之,粗劣自不待言;然而,在當年,沒有機械,沒有學識,全憑著四肢一頭,造出若干東西來,正叫做煞費苦心,這種粗劣的東西,於那時,除了使用之外,安知沒有帶些奢華的意味?安知不是藝術的起源?因為一切的藝術都是奢華的表現。
「雞無飽日,人無足時」,這句話,未免含有道學色彩,教訓我們要「知足不辱」,教訓而不聽,於是有此嘆!我想:「知足不辱」的人真聰明:人類除吃飯,拉屎,性交,睡眠之外,尚有何求?若是,吃不飽,追求而無結果,欲睡眠而未能,儘可長嘆一聲,自戀曰:「此命也夫!」說完之後,倒也輕鬆得多:這種原是可敬可愛的精神文明,或文明精神;這種精神文明,或文明精神,有惠於民族,有惠於國家者,豈淺鮮哉?民窮國弱都因為了它!
無奈人心不足?巢居穴藏,自古有之,偏要圖宮室之安;茹毛飲血,自古有之,偏要謀口舌之福。種種切切,形形色色,都從「需要」出發,而走入「奢華」途徑。世風不古,實足興悲!如果世風日古的話,那麼,逐漸返古,古之又古,以至古無可古,衣服是嫌多的了,房屋是嫌多的了,吃東西不用火燒,拉屎不用草紙抹,⋯⋯這樣,無所謂文化,無所謂藝術,無所謂奢華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切文化是從「不足」中來的,一切藝術是由「奢華」中發生的。祇須動機純正,為大我——即全人類——謀幸福,「不足」也罷,「奢華」也罷,都向著光明走,向著智慧走。
然而,「雞無飽日,人無足時」,當日的奢華逐漸變為今日的不足,我雖則沒有多大年齡,不如《惡之華》的作者有:「好似千年的回憶」,可是,還想到二十年前,坐坐馬車已算奢華了:而今呢?坐坐汽車不過如此!再過二十年,坐坐飛機又要變為平淡了。由奢華退而為平淡,由平淡退而為不足,從另一方面著眼,正是催進文化的原力。
在目下的中國,除了少數人外,群眾惶惶求生,壓根兒談不到奢華。中國一般人的生活是沉悶的,悲慘的。如果我們本著「受命於天」的無抵抗精神,坐等明日之臨止,那麼,這簡直是「束手待斃」!幸而我們還保持著一些兒火星,留存著一點兒智慧:此心未盡死,朝氣未盡滅,終想驅逐包圍著我們的黑暗,打破窒息著我們的環境!我們很明白這些火星,這點智慧,是很脆弱的:小小微風,輕輕細浪,都足致它的生命。正因如此,從百凡不足中尋些可以安慰我們的方法,從萬分簡陋中找些比較華麗的生活,倒也是當務之急;否則呢,星火熄滅,黑暗立至,一心既死,萬劫不復!
我們是從事於藝術的人。我們曾立下一個癡想:我們要使生活美術化,美術生活化。我們並沒有造出誇大難於實行的口號:什麼「改良社會」咧,「美術救國」咧!說,未嘗不可;然而但開口,不動手,固然言之者面皮老,聽之者難免肉麻了!我們要使生活美術化,先得從自身做起。這無非是從死路中打出一條生路,從非人生活中度些人的生活,從「求生」走到「求活」而已。不過,個人的力量是極有限的,與我們目的一比,正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我們集合同志,組織了一個藝風社。
「又是一個集團!」你一定要嘆氣著說。
對咧,中國集團之多正如身上的秋毫!而且,有了三個人即可成為一團體:某甲當了正會長,某乙當了副會長,某丙當了秘書;至於會員,似可不必!藝術團體之多,多於過江之鯽;黨同伐異,勝似青竹竿搗屎坑,其臭蓋不可聞!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舉,組織藝風社呢?
藝風社的特點——也是它組織的原因——至少有三:第一,掃除門戶之見;第二,純以學術為目的,無任何背境;第三,社中祇有幾位事務上的負責人,不立種種官場化的名目用以沽名釣譽。門戶之見最屬無聊,「清一色化」是瘋人的夢想。吳稚暉先生有一個絕妙的譬諭,他說:「假使『我』是一條蛆,一條野心勃勃的蛆,把所有蛆都吞吃了,變為一條絕大的蛆;到那時,舉目四矚,固然敵人絕跡,可也就感到獨自兒太枯寂了,生命太單調了」。一位有識見的園丁,必定在他的園裡,栽培種植不同的花草,而且同一時候,諸色並陳,諸香雜起,令人目悅心醉!可憐目下的中國想吞食各蛆卻無此本領的蛆蟲委實太多了,在混亂的社會中蠢蠢蠕動!而建設一個眾美並臻的花園的責任祇得由我們這班力量薄弱的人負起。
古人說:「學以致用」,這原是「學問不當空談」的另一種說法。不幸世人——有意地或無意地——誤解了它,下降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把學識抑為升官發財的工具!主張「學以致用」的人,一旦初願已酬,還能肆力於學問,精進不已;主張「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人,一旦得志,便把學問拋之腦後了。我們主張「學以致用」,而所謂「用」,即:美化人生。我們既不想顏如玉,黃金屋,以學識為工具,為敲門磚,自然不需要背境,根本就無所謂背景。
為了事務上便利起見,藝風社有幾個負責的人:倘使要稱之為「會長」,「秘書」等等,那麼,非但別人聽見了要笑,連他們自己的牙床骨也都要笑脫了!如果我們不幸有封建思想,希望做一條絕大絕大惟我獨尊的蛆蟲的話,我們就不這樣幹了,更何必乎藝風社的創設?
現立讓事實來證明我所說的三項。
藝風社成立以來,首先刊行《藝風》雜誌。藝風出版已經一年半了,它的宗旨,它的精神,彰彰在人耳目,不必多述。同時,不少朋友,——內中大部分即是藝風社同仁,——組織了一個沙龍式的文藝茶話會,刊行與文藝茶話會並行的,但獨立的《文藝茶話》月刊,發揚與藝風社類似的精神,貫徹類似的主張。所以上述三項特點,直接地由藝風社本身著眼,間接地由文藝茶話會推測,不難顯明地,充實地證明。
事實尚不只此。
如果《文藝茶話》自第三卷起,要大大地發展,與出版未久但已銷至三萬份的《美術生活》合作;藝風社除在《藝風》上出種種有價值的專號外,積一年半之努力,於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一日起,在上海中華學藝社開第一屆畫展,集合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北平、武昌、廣州⋯⋯各處的作品,融合不同的各派——最顯著的例子是南京中央大學西畫組師生的作風與杭州國立藝專師生的作風不同,——兼納國畫與西畫:實為空前的創舉!而此畫展之能實現,全賴各同仁不斷的努力:曾仲鳴方君璧賢伉儷的襄助;孫福熙兄的鞠躬盡瘁;上海汪亞塵兄等,杭州林風眠兄等,蘇州顏文樑兄等,南京潘玉良女士,顧了然兄等的幫助;各位藝術家踴躍參加;各位文學家為本刊經意題詞及撰述:對於諸位,藝風社萬分懷感,而對於公眾的贊助,也十分誠懇地感謝!至於本屆畫展各位負責人,對於本社的盡力相助,自不必說;另列名單,專誠道謝。本此精神,將來第二屆,第三屆,⋯⋯畫展,正可發揚光大,垂諸無窮;而我們靈魂中所含星星之火,竟可上燭天庭,我們腦府中所藏區區智慧,也能掀波起浪,灌惠大眾了!
南京。一九三四,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