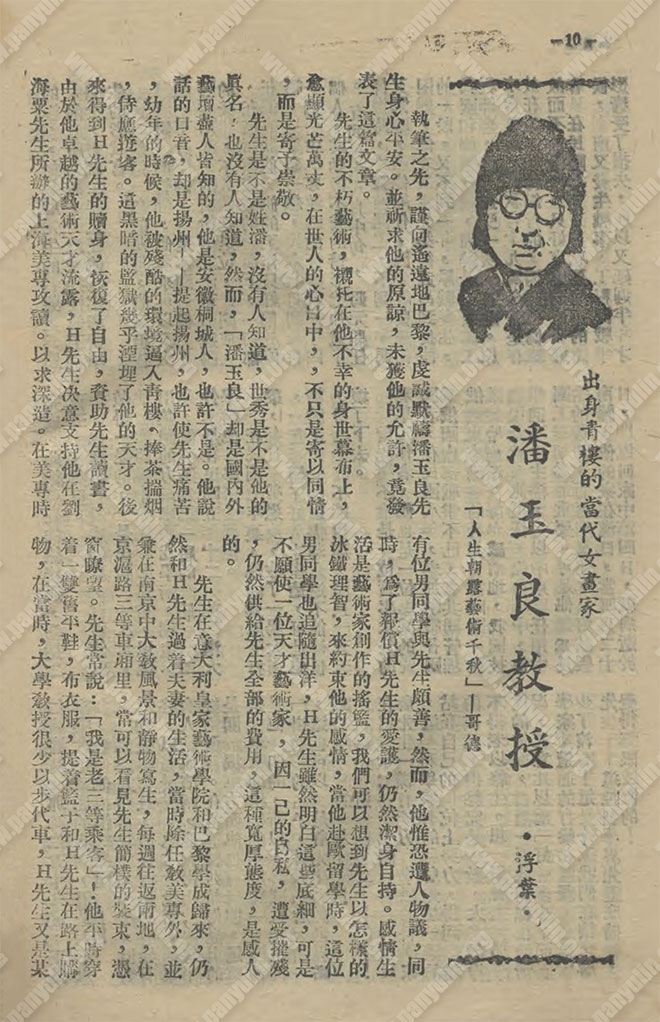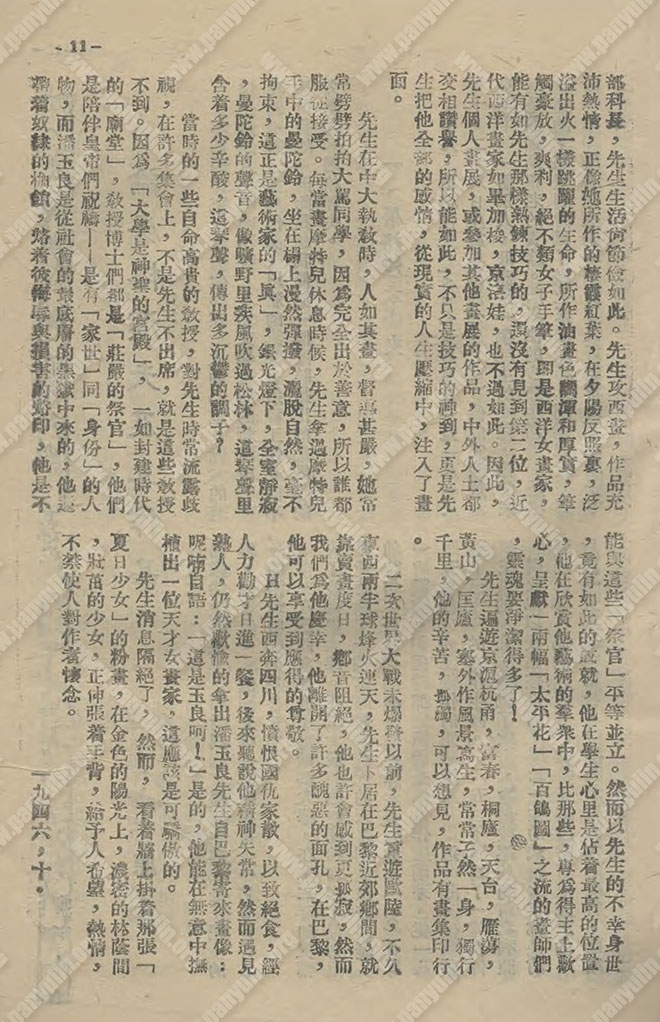「人生朝露藝術千秋」——哥德
執筆之先,謹向遙遠地巴黎,虔誠默禱潘玉良先生身心平安。並祈求他的原諒,未獲他的允許,竟發表了這篇文章。
先生的不朽藝術,襯托在他不幸的身世幕布上,愈顯光芒萬丈,在世人的心目中,不止是寄以同情,而是寄予崇敬。
先生是不是姓潘,沒有人知道,世秀是不是他的真名,也沒有人知道,然而,「潘玉良」卻是國內外藝壇盡人皆知的,他是安徽桐城人,也許不是。他說話的口音,卻是揚州——提起揚州,也許使先生痛苦,幼年的時候,他被殘酷的環境逼入青樓,捧茶揣烟,侍應遊客。這黑暗的監獄幾乎淹沒了他的天才。後來得到H先生的贖身,恢復了自由,資助先生讀書,由於他卓越的藝術天才流露,H先生決意支持他在劉海粟先生所辦的上海美專攻讀。以求深造。在美專時有位男同學與先生頗善,然而,他惟恐遭人物議,同時,為了報償H先生的愛護,仍然潔身自持。感情生活是藝術家創作的搖籃,我們可以想到先生以怎樣的冰鐵理智,來約束他的感情,當他赴歐留學時,這位男同學也追隨出洋,H先生雖然明白這些底細,可是不願使一位天才藝術家,因一己的自私,遭受摧殘,仍然供給先生全部的費用,這種寬厚態度,是感人的。
先生在意大利皇家藝術學院和巴黎學成歸來,仍然和H先生過著夫妻的生活,當時除任教美專外,並兼在南京中大教風景和靜物寫生,每週往返兩地,在京滬路三等車廂里,常可以看見先生簡樸的裝束,憑窗瞭望。先生常說:「我是老三等乘客」!他平時穿著一雙舊平鞋,布衣服,提著籃子和H先生在路上購物,在當時,大學教授很少以步代車,H先生又是某部科長,先生生活尚節儉如此。先生攻西畫,作品充沛熱情,正像她所作的棲霞紅葉,在夕陽反照裡,泛溢出火一樣跳躍的生命,所作油畫色調渾和厚實,筆觸豪放,爽利,絕不類女子手筆,即時西洋女畫家,能有如先生那樣熟練技巧的,還沒有見到第二位,近代西洋畫家如畢加梭,京洛娃,也不過如此。因此,先生個人畫展,或參加其他畫展的作品,中外人士都交相讚譽,所以能如此,不只是技巧的神到,更是先生把他全部的感情,從現實的人生壓縮中,注入了畫面。
先生在中大執教時,人如其畫,督導甚嚴,她常常劈劈拍拍大罵同學,因為完全出於善意,所以誰都服從接受。每當畫摩特兒休息時候,先生拿過摩特兒手中的曼陀鈴,坐在榻上漫然彈撥,灑脫自然,毫不拘束,這正是藝術家的「真」,銀光燈下,全室靜寂,曼陀鈴的聲音,像曠野里疾風吹過松林,這琴聲里含著多少辛酸,這琴聲,傳出多沉鬱的調子?
當時的一些自命高貴的教授,對先生時常流露歧視,在許多集會上,不是先生不出席,就是這些教授不到。因為「大學是神聖的宮殿」,一如封建時代的「廟堂」,教授博士們都是「莊嚴的祭官」,他們是陪伴皇帝們祝禱——是有「家世」同「身份」的人物,而潘玉良是從社會的最底層的黑獄中來的,他帶著奴隸的枷鎖,烙著彼侮辱與損害的烙印,他是不能與這些「祭官」平等並立。然而以先生的不幸身世,竟有如此的成就,他在學生心里是佔著最高的位置,他在欣賞他藝術的羣眾中,比那些,專為得主上歡心,呈現一兩幅「太平花」「百鴿圖」之流的畫師們,靈魂要淨潔得多了!
先生遍遊京滬杭甬,富春,桐廬,天台,雁蕩,黃山,匡廬,塞外作風景寫生,常常孑然一身,獨行千里,他的辛苦,孤獨,可以想見,作品有畫集印行。
二次世界大戰未爆發以前,先生重遊歐陸,不久東西兩半球烽火連天,先生卜居在巴黎近郊鄉間,就靠賣畫度日,鄉音阻絕,他也許會感到更孤寂,然而我們為他慶幸,他離開了許多醜惡的面孔,在巴黎,他可以享受到應得的尊敬。
H先生西奔四川,憤恨國仇家散,以致絕食,經人力勸才日進一餐,後來聽說他精神失常,然而遇見熟人,仍然歡愉的拿出潘玉良先生自巴黎寄來畫像:呢喃自語:「這是玉良呵!」是的,他能在無意中撫植出一位天才女畫家,這應該是可驕傲的。
先生消息隔絕了,然而,看著牆上掛著那張「夏日少女」的粉畫,在金色的陽光上,濃密的林蔭間,壯茁的少女,正伸張著手背,給予人希望,熱情,不禁使人對作者懷念。
一九四六,十.